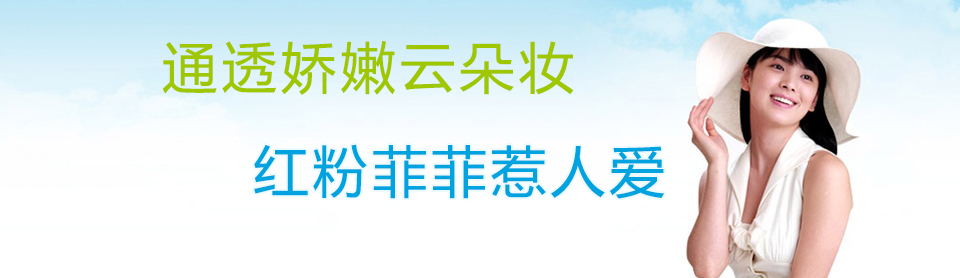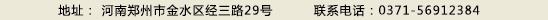家的味道卤了一只鹅
作者/。水青
当你来到潮汕做客的时候,餐桌上必有一盘"鹅肉叠莞荽"的卤味,,酱油色的鹅肉皮发亮,,咸嫩爽口的肉质,在一小撮青翠的莞荽叶点缀下,色香味俱全,再佐以旁边那碟"蒜泥醋",无不诱人食欲。这是一道潮汕人家盛情款待客人的菜品,"无鹅肉不旁沛(丰盛)",潮汕人的好客之情尽融化在其中。
鹅的种类颇多,但我所熟识的莫过于灰鹅丶雁鹅,有小巧珑玲的"漳州仔",个头高大的要数澄海的著名鹅种"狮头鹅",据说能养到一丶二十斤重,个别能长到近三十斤重。
对于鹅的习性,在乡村长大的人再熟悉不过了。过去,养几只鹅增加家庭收入的大有人在,小孩子在读书闲瑕把鹅赶到田间地头放牧,其实也是一种乐趣。当鹅们贪婪地啄食嫩绿的"鹅仔菜"时,是它们最安静最可爱的时候,这时小伙伴们的各种"游戏"就可以开展起来,女孩们从衣袋里掏出几颗溜圆的石仔,玩起了"抓科"游戏,男孩子们把赶鹅的竹竿,彼此抵在肚脐间,面红耳赤地耍起"举脐"的角斗,人鹅同乐的画面相当温馨。
"鹅是一种勇敢的动物",秦牧在他的那篇《鹅阵》里说过。他描述道:鹅群总是由一只雄赳赳,气昂昂的雄鹅领导着,当它扑翼聒噪的时候,后面的鹅们就引颈唱和着。我观察了好久觉得也的确如此。而且我曾经看过鹅首领为保卫鹅群与"狗仔"打架过,鹅生气的时候,硕大的鹅翅挺开时就象一架"战斗机",鹅嘴吼着"eee",肥大的鹅掌跳起来,狂扫淘气的"狗仔","狗仔"见状落慌而逃,这场面让我对鹅又佩服又害怕。
记得每年的"妈祖生",家家户户都得养上几只大鹅敬奉神明。我母亲总是提前一段时间从东里的牲畜市场批发来差不多"换大毛"的鹅,通常三只,买回家圈养蓄膘。每天早上赶鹅到那个"后河池"洗澡的事情,总让我思想有点负担。我害怕母亲叫上我做这件事情。除了印象中鹅打架那副尊容,让我发怵,再就是鹅一到池里就玩到发疯,通常打一个"水钻"就不见踪影,弄丢了怎么办?这时候,村里扎堆养鹅,满池的鹅,各家各户各给自家的鹅做个"记号"可以识别。我家的鹅脸上都涂上红铁油,就象个打了腮红的娘们,非常醒目。把鹅赶入池子里的时候,我总是屏住呼吸,目不转睛地盯住它们,它们洗得开心的时候,那知道我紧张得要命,好几次它们钻到水下再浮上来的时候,我已经盯混了找不到它们,只能哭着回家,而母亲总能奇迹般把它们找回来。
农历三月廿三前一天,乡里的鹅声嗄然而止,满乡尽是鹅肉香。拜"妈祖"的场面就是一场赛大鹅的场面,精心卤制的鹅肉散发着八角茴香桂皮......的香味。供奉神明的仪式完毕后,整只鹅便被分成几部分,装入竹编的"春圣""花篮"去做"人客",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,送给亲戚朋友的鹅肉不仅是带去一顿美味,更多的是传递着浓浓的亲情。
老人们食着鹅肝总喜欢嘀咕一句:"亥爷得份妈祖福",奴仔啃着"鹅脚翅"听了似懂非懂,想一想也是,一年到头难得食上一回鹅肉,没有拜"妈祖"肯定是没有鹅肉食的,不象现在,鹅肉成为"家常便饭"。
在我的记忆中,乡里有一老妇由于经济困难,却有一份尊敬神明之心。她一时有了歪主意偷了别人的鹅,不料被发现,那时乡里干部对她的惩罚就是怀抱偷的鹅游遍乡里巷。陪她游巷的有我们一群"奴仔",她神情凄凉羞愧地行走着,怀里的鹅不时伸出长长的鹅颈,勾着头窥探着后面的我们有没有走好路......
"无鹅肉不旁沛(丰盛)",这句俗话道出了我们对于鹅肉的喜爱,"酒起,鹅肉剁",更是表现出潮汕人客情之豪爽。
据了解,早在古代的婚嫁聘礼必送一对鹅做为"奠雁礼",以鹅代雁,寓意好意头,象雁一样齐行有序,不失其节,终身不再偶。鹅,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良禽是贞禽。
潮汕人喜食鹅肉的历史也是一部经济发展史。鹅做为发展经济产业链,己经产生出许多行业深入到大众生活。"潮汕卤鹅肉"的招牌走向全国,甚至走向世界。
街头巷尾的"鹅肉饭""鹅肉面"的鹅肉店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滋生。"玖悦股份"的掌门人王晓霞更是把潮汕卤鹅肉与外国红酒巧妙地结合在一起,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澄海闻名狮头鹅,城北人陈唪嗳父子更是把狮头鹅的形态,习性,用舞蹈的形式体现出来,把牧童放牧鹅的温馨场面刻划得唯妙唯肖,生动有趣,舞蹈"双咬鹅"把潮汕人爱鹅之深厚感情推向了更高境界。
鹅肉的烹调手法五花八门,我食过"烧鹅肉","甜鹅肉".......就是觉得没有我们潮汕正宗的"卤鹅肉"耐人寻味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qianjiangyoumendaxia.com/shxg/10260.html